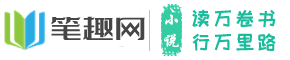第一乐章。(2 / 2)
而关珩,早已给予了他足够的适应时间。
那是一场几乎令人窒息,死去的征伐。
房间里乱得不能看,他们最后甚至只能躺在地板上。
宁秋砚连眼皮都抬不起来,也不知道最后都发生了什么,恢复意识的时候,他正靠着温暖的炉火。
他伸出手去触碰,好奇为什么是它能在地板上燃烧。
身后的关珩却把他的手拿回来,下巴抵在他的头顶,低声说“是假的”。
手指亲密地划过白皙的手臂内侧,那行深蓝的拉丁文字母。
其意为“山巅的月光”,是纪念去世母亲的刺青。
宁秋砚好像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铭记生活里一些想要记住的事,用自己的身体,皮肤。耳后的爱心是,手臂内侧的拉丁文是,耳垂上关珩给的耳洞也是,很难说以后还会不会增加别的。
明明那么脆弱,却又对自己有奇怪的破坏欲。
宁秋砚和他这个年纪的大部分男孩一样,都是叛逆的矛盾体。
但是他又太乖。
无论在外面如何张牙舞爪,特立独行,在关珩面前都会顺好毛,无所不从。
如果就这样将他永远地留在渡岛,禁锢在这三楼,禁锢在这房间的大床上,他也只会睁着那双湿漉漉的、小狗般单纯的眼睛,只要关珩开口,他便会无条件地答应。
因为他是关珩的。
“抬手。”关珩说。
宁秋砚快碎了,但还是翻过来,听话地抬起了手。
火光在他的睫毛上跳跃,关珩披散长发,低头吻了他的嘴唇,奖赏似的说“乖孩子”,轻得如同遥远的呢喃。
细链发出声响,双手重新扣在了一起。
关珩细致地分开他。
温柔继续。
但不再让他随意触碰。
宁秋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,睡了个昏天黑地。
大概是累极,他没有怎么做梦,醒来才发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。人躺在被子里,穿着自己的衣服,床头的小黄花换了,是一支白色小苍兰,不知道在这种天气是怎么摘到的。
那些戒指都放在桌面上,红宝石的耳钉也在。
他猜是关珩抱他下楼的。
起床时身体酸软得厉害,宁秋砚的四肢都在发抖,却不是因为饥饿,而是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。
好在除了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痕迹,他一点也没有受伤,所以只面红耳赤地缓了一会儿,还是穿戴整齐去洗漱。
宁秋砚先去了一趟厨房,白婆婆不在,一位婶婶告诉他白婆婆去了农场,还有几天就春节了,他们需要在那里将准备好的一些食材收好带回来。
岛上不仅有养殖场,也有温室农场,宁秋砚之前听说过,但那里有些远,他还一次都没去过。
厨房里倒是随时都有吃的。
宁秋砚自己动手做了份简单的食物,勉强恢复了一些力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