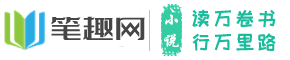82(2 / 2)
回到家中,朵儿姐不在,查到了几家被游击将军迫害过的人家,朵儿姐挑了一家,已经上门游说去了。
谢寒梅让人把名单给自己,“我瞧瞧,也登门拜访一家。”
“东家,您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,铁打的人也熬不住啊,花大掌柜已经去了,您就眯一会儿,养养神也好啊。”跟着她的亲随劝慰道。谢寒梅身边跟着的人已经换了四轮,她自己却一直熬着。
谢寒梅摆摆手:“时间不等人,输赢在公堂之外,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不要劝啦,赶紧去拿名单。”
亲随无法只能拱手退下,去书房取名单。
等回来的时候,亲随看见谢寒梅趴在桌子上,身体规律起伏,隐隐有鼾声传来。太累了!身体压迫着鼻腔,素来不打呼的谢寒梅,此时也累得打起呼噜。
亲随不忍心叫醒她,就在门边等着。他们都清楚,花果不过是谢寒梅一个雇工,即便跟着时间长,也只是雇工,更别提花大那个烂人和他婆娘那个拎不清的蠢货。谢寒梅对花朵、花果早有救命之恩,如今花果落难,谢寒梅倾尽全力相救,令他们动容。以此类比,若是他们有朝一日落难,东家也会如此相救。
亲随静静站在门外等候,却听得脚步声飞快靠近,门房过来看到亲随比了个禁声的手势,立即会意,小声凑到他耳边道:“老家贺进士来访。”
亲随抬头看了眼黑黢黢的天,“这么晚?可说了什么事?”但他也明白此时正是关键时候,哪里顾得上天色。可东家都累得睡着了,该不该叫醒呢?会不会怠慢了进士老爷?
亲随还在犹豫,听到隐约说话声的谢寒梅已经惊醒过来,问道:“出了什么事?”
亲随立刻扬声道:“东家,老家贺进士前来拜访。”
“贺广泰?请他到客厅安坐,我去后堂洗把脸。”谢寒梅绕到里间,在水盆里浇了两把冷水在脸上,彻底醒过神来,又立刻绕出去。
贺广泰进门的时候,就见谢寒梅鬓边微湿,两颊通红,眼睛里全是血丝,活似两只兔子。
“你多保重。”贺广泰脱口而出。
谢寒梅伸手做请的姿态,等他落座后自己也坐下,勉强勾了勾嘴角,“多谢关怀。不知你深夜来访,有何要事?”
“你我之间,还要如此生疏吗?”贺广泰知她忙碌疲惫,也不绕弯子,开门见山道:“果子的事情都传到老家了,我又听说了你当日飞马过大街,猜你肯定到这边来想办法,就一起过来,看能不能帮上忙。”
他干脆,谢寒梅也不做谜语人,笑道:“多谢。府学能有如今声势,多亏你帮忙。”
“果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,都是同乡,能帮一把是一把。”贺广泰说得诚恳,“等后日过堂的时候,我也会去旁听。如今我身上虽无官职,但有进士功名,也能说得上话。”
谢寒梅又谢他一回,什么“看着长大的”,贺广泰常年在外求学,花果一直在老家,他上哪儿看去?谢天谢地,贺广泰如今正处于考中进士回家展墓、祭祖的假期,总算有个身份合适的人帮腔。
感谢的话车轱辘来回说,说了几遍,两人也不好意思再说,就这样沉默着相对而坐,气氛有些尴尬。
半响,贺广泰道:“我之前说的事情,你考虑好了吗?若是你有官眷的身份,遇到这种事情,就不会如此麻烦。”
谢寒梅使出拖字诀,苦笑摇头:“是啊,不经此事,不知身份的重要。只是我如今实在忙乱,脑子里一半水、一半面,这一晃荡——一脑袋浆糊。等把果子救出来,再细细思量。”
贺广泰颔首,“不急,我还有两个月的假期,从这里乘船顺水而下,再走运河上京只需一个月。希望……算了,等果子救出来再说吧。”
谢寒梅感激得望着他,满是红血丝的眼睛里有水光闪过,千言万语只凝成两个字:“多谢。”
贺广泰看她如此疲累,不好多留,很快告辞离去。
谢寒梅坚持送他,站在门口,等马车再也看不到,才回头对亲随道:“名单呢?赶紧的!”
输赢在公堂之外。
最后一天,谢寒梅、朵儿姐和贺广泰分别守在衙门附近、码头、府学三处依江春,用力宣扬美少年反杀将军案,尽力多找一些多自家有力的证据。
但是,时间转瞬即逝,很快就到了过堂的日子。
知府大人高坐明堂,头上悬挂着“明镜高悬”的木色黑底大字匾额。
“啪——”惊堂木一拍,审案正式开始。
衙门外已经里三层、外三层围了许多人,甚至还有帮闲、跑腿、小厮挤着换班,给等在旁边酒楼、客栈的主人家回禀消息;说书人之流更是多不胜数,这都是日后的好生意;还有府学学子,这些人对花果的遭遇颇为同情,都是来声援他的。
死去的游击将军儿女年幼,将军夫人不知是为了施压,还是给知府大人脸面,亲自上堂。她身为官眷,有敕封在身,坐着。
贺广泰怕花果吃亏,以同乡的身份旁听,他当场提出,知府不好回绝。贺广泰还未授官,但有功名,站着。
花果两个衙役押到堂前,手上、脚上皆有镣铐,刚到正堂,就被两个衙役一脚踢在小腿扑倒在地,跪着。
惊堂木一响,谢寒梅就感觉自己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知府在审案、将军夫人在哭诉、花果声嘶力竭分辨什么,还有贺广泰拱手向知府大人陈述……谢寒梅等人找的证人一个接着一个上堂,将军府找的证人一个接着一个指认,围观审案的人还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喧闹,仿佛他们也参与了这场审判。
明明身边如此喧闹,谢寒梅却觉得什么都听不到,她看到花果消瘦、单薄的背影,想起昨晚在牢里见他时,花果坐在脏稻草上,昂着头,头顶狭小的窗户,透出一束光,照在他身上:“我才不死!我偏活着!连阴百日,也有天晴;冬长三月,早晚打春,我要眼睁睁看着那些丧尽天良的人遭到报应,才肯闭眼。”
知府嘴唇蠕动,听不清说的什么;将军夫人骄傲得掀开幕僚,趾高气昂瞥了外面的乌合之众一眼;贺广泰着急上前两步,拱手想要进言,却被知府挥手制止;门外学子们义愤填膺,纷纷振臂高呼……
好像有声浪在耳边炸响,但却一句也入不了谢寒梅的心,她觉得自己漂浮在半空中,听不见分毫。
就在此时,一切仿佛被按下的暂停键,围堵在衙门口的众人如摩西分海一般向两边散开。两队衣着整齐的执仗人排开众人,为后方主家开路。一位留着长须、皮肤白皙、眉眼瘦长的中年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常服,但只看衣料就知尊贵。
原本高坐的知府急忙整理衣冠,躬身小跑近前,深深作揖。在场所有人都矮了一截,士绅弯腰、百姓跪拜。
“都免礼吧。”
谢寒梅的听觉突然回来了,与方才的喧嚣相比,此时大堂静得落针可闻。
“谢王爷。”知府起身,恭敬垂首询问:“不知王爷驾临,有失远迎,还望恕罪……”
蜀王殿下摆摆手,“行啦,这美少年反杀将军案,都传到我耳朵里了,整个成都府沸沸扬扬,我岂能不来听一听。”
“抬起头来,让本王瞧瞧。”蜀王轻声吩咐,花果闻言抬起头来。
“老蒋也是眼神不好,不过清秀之姿……不过,这双眼睛……倒是有神采。”蜀王低头瞧了一眼,随意品评着受害人的相貌,又转头问知府:“怎么判的?”
知府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若是满意他之前判的,蜀王殿下就不会出面了;可让他当场改口,知府面子上绷不住。左右拿不准蜀王殿下的意思,知府更加不敢说话。
蜀王嗤笑一声,“行啦。听说此子从将军府逃脱,直奔县衙,可见对官府有信任;可他擅杀官员,不可不惩——这样吧,念在事出有因,流放三百里,以儆效尤。”
蜀王说完,环视一周,尽皆俯首,谁敢多言?
方才叫嚣着要让花果去死,要依江春关门的将军夫人亦低头垂目,恭敬温顺。
蜀王察觉人群中有人看他,转头过去,只见一双盛满火光的眼睛,直愣愣的看着他。若是面目丑陋的愚民,蜀王自然不悦;但见是一名妙龄少女,蜀王也就一笑而过了。